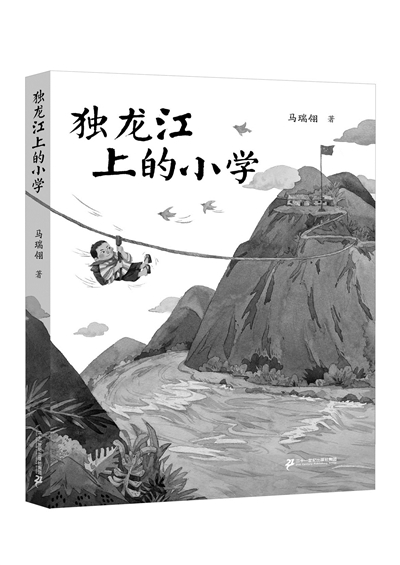
馬瑞翎的長篇兒童文學小說《獨龍江上的小學》,是我讀過的眾多取材于秘境獨龍江的既有作品中最好玩、最有趣的一部。這部作品,故事有趣,人物有趣,語言有趣,就連我跟這本書的結緣也非常有趣——
那天取書后走出快遞站,我進了隔壁理發店,邊看邊理發。沒想到小說第一章居然是“阿鼎剃頭”——主人公阿鼎找獨龍峽谷里的骨科醫生剃頭,醫生只會剃光頭,而且是用鐮刀。以前還有人用砍刀,遠處的獵人以為那是要行兇,果斷開槍,從此結束了獨龍族砍刀剃頭的歷史……我把剛看完的故事開頭講給了剃頭師傅聽,結果圍上來一堆人,說要買這本書。師傅說,書留下,理發錢不收了。
出門留下20元,拍了一張照,發給作者馬瑞翎。她說,你得讓師傅用鐮刀啊!
以上,是我發在朋友圈里引起“微友”圍觀、打探作者與書的一段文字。我就這樣,在國內疫情向好之時,從一本書,走進了“最后的秘境”獨龍江,走進了“獨龍江上的小學”,走進了獨龍族少年阿鼎的斑斕世界。
小說講述了獨龍族少年阿鼎的成長故事:從他不愿上學,到迷戀上學,并且發愿要“使勁學、狠狠地學”;從他跟著爸爸“過溜索”,到獨自踏上艱難求學路,再到即將踩著“彩虹橋”上學;從他進入擔當力卡山上的“一師一校”上學,到即將融入獨龍鄉“好大”的中心學校去集中上學……上學是小說主線,學校是故事舞臺,主角當然就是阿鼎和他的同學、老師以及阿爸阿媽。
獨龍族,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現代社會的一個民族。在時間深處,在大山深處,在江峽深處,它“藏在深山人未識”。在新時代感召之下,在“一個也不能少”的中華全民族告別貧困的歷史主潮中,曾經隱忍卑微的獨龍族,從幕后走到臺前,走到了新時代聚光燈下,閃耀出質樸而動人的光芒,為世人所矚目。如果說以上是《獨龍江上的小學》的寫作背景,那么阿鼎們的命運正是這個民族的一個“切片”。作者諳熟于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尺幅興波的小說藝術規律,調動了大量的對比和隱喻,來渲染和放大“切片”效應。一方面是圍繞“必須要上學”展開的:為了“誘惑”阿鼎上學,阿爸陪他剃頭、守苞谷地……另一方面是圍繞“為什么要上學”展開的:父輩結繩記事的尷尬、大江溜索斷裂的慘劇、村子擺棍講理的囧事……正是這些承載了歷史記憶的生動細節,無聲地述說并反證了一個民族走向蘇醒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
這是一部返璞歸真又結構奇巧的小說。小說以少年視覺打量世界,那個世界保持著原初本真的模樣兒:植物是神仙的“汗毛”,動物“懂”得人的心理,人要是過一次溜索,就會長出一對飛翔的翅膀。作者在敘事結構上下了很大功夫,她采取了一種非常巧妙的“連環扣”敘事,每個章節的結尾,正好“頂”出下一章節故事的開頭。全書沒有緊張曲折的完整故事情節,卻能讓一個個碎片般的小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故事正好絲絲入扣地對應了獨龍江峽谷的現存秩序和生活法則。
我還特別贊賞這部小說通篇那富于鄉土氣質的詩性語言,其語言基調比較準確地把握著追求傳統民族民間語言與現代漢語言的契合,善于運用神話思維和詩性唯美相雜糅的、民族方言和規范漢語敘述相交織的、節奏時而短促時而舒緩的詩性句子,形成一種古老而又現代、唯美而又質樸、繁復而又簡潔的文本,表現出時代滄桑和“人口較少民族”起伏的歷史感,從而使作品對語言基調的選擇和把握進入到比較自由成熟的境界。
關于秘境獨龍江,我去過兩次。一次是那條舉世矚目的獨龍隧道通車的第二天,我隨一個攝制組進山拍攝獨龍族“卡雀哇”節全過程;更早的一次則是隨中國作家團走進峽谷“采風”,那次我認識了馬瑞翎,之后又陸續讀到過她以怒江和獨龍江為底色的那些作品。從《怒江往事》到《獨龍江上的小學》,可以感知,這是一個懷揣鄉愁走天涯的女人,她有著不自知的悲天憫人又樂觀向上的情懷,有著對自己曾經朝夕相處過的秘境邊緣人群的天生的“共情”。她在完成《獨龍江上的小學》后說:“任何人的童年都有歡樂的一面。作品中赤貧孩子身上所散發出的人性的光輝,尤能觸動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使人感到安慰。”大山大江曾經屏蔽了一個民族,這個族群被驅隔、拋甩在現代文明世界之外。這個“化外之地”,既有“桃花源”的鄉愁特質,更多的卻是封閉中的匱乏、落后和無奈。從“獨龍江上使人愁”到“鄉愁寫罷讓人喜”,作者以活潑生動的文字,敘寫了一個孩子也是一個民族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巨大進步。
我欣賞這樣的作品。
(作者系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著名兒童文學評論家)
《中國教育報》2020年05月27日第11版
工信部備案號:京ICP備05071141號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24
中國教育新聞網版權所有,未經書面授權禁止下載使用
Copyright@2000-2022 m.junhanjc.com All Rights Reserved.